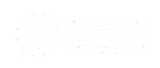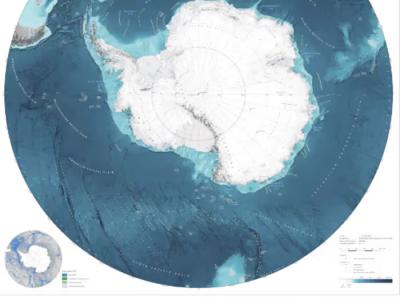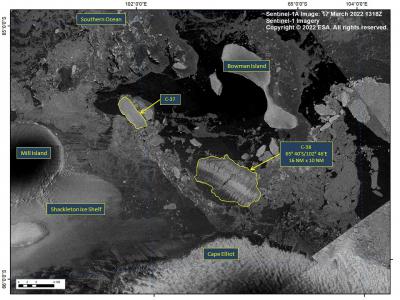亚马逊的捍卫者:凯亚波人

亚马逊的捍卫者:凯亚波人
据美国国家地理:在这里,我们很容易会以为自己回到了过去,以为我们脱离了现代社会的束缚进入部落生活,进入原住民文化的最后堡垒;这个文化虽然长期受到威胁,却仍生气蓬勃、完好无伤、昂然挺立。数百年前,最早深入亚马逊盆地东南方的外来者包括传教士、寻金客、奴隶贩子、豹皮猎人、橡胶采集业者、还有被称为「桑塔尼斯塔」的野外探险家,那时他们只能艰难地驾着船只沿河而入。今日,我们则是在干季尾声的一个9月早晨,在良好的天候下搭乘西斯纳单引擎小飞机抵达。
飞机在巴西边城图库马附近穿过森林火灾的浓烟前进。我们以大约185公里的时速向西南飞行了半小时,越过蜿蜒而泥泞的布兰科河。转眼间,大火消失了,道路没了,树木被伐除一空、点缀着白色牛群的牧地也不复见,只剩下一片杳无人迹、迷雾缭绕的森林。我们下方就是凯亚波印第安人的家园,这片区域由政府划定的五块毗邻土地组成,加起来的面积相当于三个台湾。这是全世界最广袤的热带雨林保护区之一,由9000名原住民掌管,大部分的居民都不识字,主要仍靠着原始技能维生,生活在仅以河流和荒湮小径相连的44个村落里。 《国家地理》杂志工作团队的目的地是其中最偏远的村落之一,肯强村,意为「耸立之石」,得名自我们眼前的这座深灰色山岳。这座山仿佛鲸鱼破水般从一片绿色树冠中拔起约245公尺。山后不远处是波光粼粼宛如发辫的伊里里河,它是亚马逊河主要支流辛古河的最大支流。飞机转向降落在泥土跑道上,缓缓滑行经过环绕一片沙地广场而建的小菜园与茅草屋。
我们下了飞机,十几个只穿着短裤或什么也没穿的孩子一拥而上,蹲在机翼的阴影下。倘若与他们眼神交会,他们就会咯咯笑地移开目光,然后再偷瞥你是否还在看他。其中几个年纪最小的孩子,耳朵上都穿有马克笔粗细的圆锥形木栓。凯亚波人会在婴儿的耳垂上打洞,以象征性地增进孩子对语言和社交的理解能力。在凯亚波语中,表示「愚笨」的词语是「阿玛可莱给特」,也就是「没有耳洞」之意。
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卸下行李,里头包括准备给主人的礼物:鱼钩、烟草,和10公斤捷克制造的高级串珠。
芭芭拉.席莫曼是凯亚波计画的主持人,这是加拿大国际保育基金会和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共同计画。席莫曼带我们认识村长普卡提里,中年的他戴着眼镜、穿着短裤和夹脚拖鞋。 「阿卡提美,」他边握手边以凯亚波语打招呼,接着又补上一句他到北美洲时学到的几句英文:「哈啰,你好吗?」
肯强村看似古老,但其实自1998年才建成。当时村长普卡提里和他的追随者因为伐木纠纷而迁离了伊里里河更上游处的普卡努村。凯亚波人往往透过人类学家所谓的「分家」来解决冲突或减缓某个区域内资源不足的压力。村庄现在的人口是187人,尽管外观看似传统,它其实配备了一些会让普卡提里的祖先大感惊奇的设施:政府建造的护理站里有一台发电机;刺网护栏内的一列太阳能板;架设在半截棕榈树上的碟形卫星天线。少数人家的茅草屋里还有电视,他们喜欢观赏部落仪式的影片和巴西肥皂剧。普卡提里带我们参观一栋巴西政府在几年前盖的校舍,这栋水泥建筑被漆成开心果仁的黄绿色,有两间教室、瓦面屋顶、百叶窗,还有抽取井水的豪华冲水马桶。我们就在校舍的阳台上扎营。
日温开始升高,村落里弥漫着慵懒的宁静,偶尔才被互相叫嚣的狗和为明天的日出做准备、像在唱歌剧一样啼叫的公鸡所打破。在中央广场,也就是「卡伯特」的边缘,女人们坐在芒果树和棕榈树荫下忙着剥坚果壳,把鱼裹在叶子中、埋进煤炭里闷煮。有些人则出外到因为烧垦法而土地焦黑的菜园照料栽植的木薯、香蕉和蕃薯。一名乌龟猎人从森林返回,依循凯亚波的习俗朗声高歌,以宣布他捕到了村民的重要食物来源:陆龟。向晚时分,热气消退。一群年轻战士踢着足球。大约20名颈子戴着一圈圈彩色串珠的女人把孩子缚在腰臀间,聚集在卡伯特,开始踩着相同的舞步吟唱。男孩们拿弹弓朝小辫鸻和燕子发射石头,其中一名男孩击中一只白喉王霸鹟后把它抓在手上,有着黄色胸羽的鸟儿倨傲地怒目回视,仿佛是哥雅名画里不畏行刑队的那名农夫。几户人家慢慢移向伊里里河准备例行的黄昏沐浴,但是河里有凯门鳄,所以随着天色渐暗,他们并未多逗留就上岸了。在位于南纬8度的此处,血橘色的太阳迅速沉落。吼猿的咆哮与有如拨号声般嗡嗡不断的蝉鸣相互交叠,泥土的气息飘散在夜晚的空气中。
乍看之下,肯强村犹如伊甸园一般。也许当真如此。但这不表示凯亚波人的历史是在世外桃源中度过,或他们未曾经历几乎所有南北美洲原住民部落都曾遭遇的迫害和疾病。 1900年,也就是巴西共和国成立的11年后,凯亚波人口约有4000人。当矿工、伐木工、橡胶采集者和牧场经营者大批涌进巴西境内,传教组织和政府部门也展开对这些原住民部落的「招安」工作,以衣物、金属壶、弯刀和斧头等物品换取他们的信任与合作。但与外界的接触往往在不经意间将麻疹和其他疾病带给了缺乏天然免疫力的原住民。 1970年代末叶亚马逊横贯公路建造之后,凯亚波人口已衰减至1300人左右。
尽管受到冲击,他们却从未被打倒。 1980到90年代,凯亚波人在一批具有传奇色彩的酋长领导下团结起来,这些酋长利用凯亚波的战士文化达到政治诉求。罗普尼和米卡隆提等领袖以军事化的精准手法组织抗议活动,开始施加政治压力。他们甚至会杀害闯入他们土地的人。凯亚波的战士团体将非法的牧场和金矿业者驱逐出境,有时他们会让对方选择是要在两小时内离开印第安领土或当场受死。战士控制了渡河要塞,在边界巡逻。他们会扣押人质,并把掳获的闯入者剥光衣物后遣送回镇上。
为了争取自治权和土地自主权,那个年代的酋长不仅学习葡萄牙语,也争取到保育团体和名人的协助,例如摇滚巨星史汀就曾与酋长罗普尼(又名拉欧尼)一起旅行。 1988年,凯亚波人让原住民权益被写入新的巴西宪法,后来,他们的领土也获得法律承认。 1989年,他们因为在辛古河进行的卡拉拉欧水库计画会导致他们的部分土地遭到淹没而发动抗议。保育组织也加入凯亚波人的行列,一同参与了现在以「阿塔米拉集会」为人所知的大型示威活动,让原本要在亚马逊流域建造六个水坝的计画因此取消。 「在1989年的阿塔米拉集会上,凯亚波领袖很高明地将凯亚波人的战士传统,转化为20世纪的公关操作,」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人类学家史蒂芬.薛兹曼说。 「他们改变了谈判的条件。」
如今凯亚波人口迅速成长。从猎枪、铝制机动船,乃至脸书网页,他们展现了一种精明的能力,能够从与他们相邻、靠现金运作的社会吸收科技和做法,却又不失去他们文化的本质。康乃尔大学的泰伦斯.透纳是著名的人类学家,也是凯亚波文化专家。在他的协助下,凯亚波人开始利用摄影机来记录部落的仪典和舞蹈,也拍摄与政府官员的会面。他们擅于将外界元素融入自身文化中,其中一个小例子是,凯亚波的串珠工人现在流行使用的图案就取材自巴西银行的标志。 1980年代,几位部落酋长与金矿业者合作,并在1990年代出售了桃花心木的砍伐特许权,让一些保育人士大感失望,不过,这些酋长后来都后悔缔结了这种商业合作,这些关系也大多已经终止。
最重要的是,凯亚波人学会组织起来,放下偶有的摩擦,团结一致达成共同的目标。因此,在巴西境内尚存的大约240个原住民部族中,他们可能是最富有,也最有势力的。他们的仪典、亲属系统、使用的杰语、对森林的知识以及天人合一的观念,都保存完整。其中也许最关键的一环,就是他们还保有自己的土地。 「凯亚波人并不是以败战者之姿迎接21世纪。他们没有自我矮化,」席莫曼告诉我。 「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传授传统文化的技能和仪典是一回事;但对于沉迷iPhone、享受从店家购买食物的便利感的年轻世代,要如何激发他们重视制造箭毒、高叠陆龟,以及如何用毒树藤减低水中含氧量来使鱼昏迷等知识,却又是另一回事。许多肯强村的居民依然对传统服饰、串珠工艺和祖传习俗兴趣浓厚,但并非人人如此。就算是,外来的威胁仍旧可畏。
「巴西政府正尝试通过一些法律,内容是未来使用原住民的河流作为发电或采矿之用,或什至得重新画分土地时,都无须经过原住民同意,」绰号「宾哥」的阿德里亚诺.耶罗左林斯基说,他是代表凯亚波22个村庄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去年6月,400名凯亚波酋长在科克莱莫罗村针对一系列政令、条例、法案及宪法修正案誓言反对,因为这些法案会削弱他们的土地控制权,并让任何原住民团体都无法再增加领土。这些法案让人想起北美原住民遭到背叛及家园被强占的悲凉历史,许多人也认为背后的目的是为了让采矿、伐木和农业利益团体可以规避原住民权益问题,因为受到巴西宪法保障的原住民权益,对这些团体造成许多「不便」。在这场政治角力的诸多面相中,此刻最让凯亚波人感到痛苦的,恐怕就是要阻止他们以为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挡下的一项计画。卡拉拉欧水库计画这回换了新名字卷土重来;现称为「贝罗蒙奇水力发电厂」。
拜访肯强村的第二天,我们与两名凯亚波射手沿伊里里河航行,他们分别是育有三女四男、25岁的欧凯特,以及有两男五女、38岁的梅克里。梅克里戴着黄绿色的串珠臂环和系了一根蓝色长羽毛的头带。我们搭乘两艘加装了拉贝塔马达、可在干季沿浅水航行的铝制小艇离岸。有些河段仿如午夜的镜面般漆黑而平静,有些则像是茶水,或在褐色的巴西地盾岩上漫流,或潺潺穿过和缓的湍流,或蜿蜒于一片前寒武纪的花岗质巨砾之间。
我们来到一片宽广如河湾般的水域时,欧凯特把船驶往伊里里河西岸的空地旁,熄了引擎。我们爬上岸。欧凯特和梅克里优雅地钻进森林里。梅克里肩上扛着弓箭,欧凯特带着猎枪。我挨低身子、左躲右闪地通过带刺的蕨类植物和掉落的树枝,途中还得一直停下来拔掉缠在身上的藤蔓,并且说服自己,不是每个落叶堆下都有剧毒的响尾蛇潜伏。这样前行了五分钟后,我已经不知道哪边是东哪边是西,没有概念河在哪里,更不可能一个人找到返回船只的路。
我们追踪到一个隐约的猎物踪迹。梅克里指给我们看猯猪的排遗,那是种小型的野猪,在它的行迹旁有一片被踩踏过的地面,它曾在那儿睡觉。这些痕迹在梅克里眼中都很明显,就像超市肉品区对我而言是再好认也不过一样。他和欧凯特往前方急奔。 15分钟后传来一声枪响,然后又响起两声。
等我赶上他们时,只见一只猯猪已躺在树叶堆上一命呜呼。梅克里把一块树皮搓成绳索,绑住猯猪的脚。接着又劈下一条皮带形状的树皮,绑住它的前后腿,然后把猎物甩到肩上。
留在村里的凯亚波人则忙着捕鱼。他们先堵住沙洲上蝼蛄巢穴的出口,捕到一批蝼蛄后,再把它们穿在鱼钩上,用来钓红臀点脂鲤。接着他们在桃花心木制的独木舟船桨上把红臀点脂鲤剁碎,当作鱼饵来抓孔雀鲈和尾斑石脂鲤。他们在河岸上以打火机点燃排放整齐的木柴,升起营火,再用刚削好的木签串烤午餐。
下午3点左右,我们乘船逆着微弱的水流朝肯强村驶去。梅克里斜倚在船头,背靠着桃花心木桨,翘着脚,双手交扣托着后脑勺,望着催人欲眠的水流,仿佛是个在漫漫长日过后搭火车返家的通勤族。
那天晚上,普卡提里酋长带着手电筒悠哉悠哉地晃来我们的营地。 「白人文化里我们会需要的东西,不过就拖鞋、手电筒和眼镜而已,」他友善地说。他很有幽默感。你绝对猜不到,他有两个孩子在肯强村创立不久后死于疟疾。
在村庄的人口普查中,普卡提里的生年登记为1953年,上头也列出他太太、他们38岁的女儿和三个孙子的名字。他说他出生在肯强村西方的诺夫普罗格莱索镇附近,当时凯亚波人尚未与外界接触。当普卡提里的村落被来自包乌村的凯亚波人袭击,他的母亲和襁褓中的妹妹都遭到杀害,他和他的兄弟则被带到包乌村养大。他说当时他大约六、七岁,一直到十二、十三岁时,才跟他的父亲重逢。 「我们很高兴。我们都哭了,」他说。
普卡提里从传教士那儿学了一些葡萄牙语,然后被「印第安人保护服务」招募,参与协助他们的安抚计画。印第安人保护服务是「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的前身,基金会现在是代表巴西原住民利益的政府单位。 「在与外界接触以前,我们互相残杀,每个人都活在恐惧里,」他说,「不用说,现在情况确实好多了,因为大家不会再拿着战棒招呼别人的脑袋。」
但普卡提里还是提出我一再听到的感叹:「我担心族里向白人看齐的年轻人,他们剪短头发,戴上你在镇里看到的那些愚蠢的小耳环。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知道如何制作涂箭头的毒药。在巴西利亚,大家总对凯亚波人说他们的文化迟早会流失,还不如早点了结。长者必须站出来,对年轻人大声呼吁:『不要用白人的东西。白人有白人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如果我们开始过度模仿白人,他们就不会惧怕我们,就会来夺走我们拥有的一切。但只要我们能维持传统,我们就会有所不同;只要我们有所不同,他们对我们就会有点害怕。」
夜色已晚。普卡提里起身道了晚安。明天是个大日子。曾在数十年前为了保护这片森林而四处奔走的凯亚波领袖米卡隆提和伟大的罗普尼,将要前来肯强村,与那始终阴魂不散的水坝计画重新开战。
这项萌生于40年前军事独裁时期的计画,经过了长达40年的研究、抗争、修改、法院判决、撤销判决、封锁、国际呼吁,再加上《阿凡达》导演詹姆斯.卡麦隆为此拍摄的电影和几番诉讼后,耗资140亿美元的贝罗蒙奇发电厂终究还是在2011年开工了。这座含括了运河、蓄水库、堤防和两个水坝的复合建设就位于肯强村北方约500公里的辛古河上游,那里有一个名为「大伏尔塔」的巨大U形河湾。这座电厂最高可以生产1万1233百万瓦的电力,预计于2015年启用,却也让巴西国内分为两个对立阵营:拥护者表示水坝可以提供必需的电力;环保人士则谴责它是一场社会、环境和财务的大灾难。
2005年,巴西国会投票通过重启水坝建设,理由是水坝提供的能源有助于确保这个正在快速成长的国家安全。 2008年,凯亚波人和其他受到水坝计画影响的部族再度于阿塔米拉集会。根据当时的新闻报导,一名巴西国有电力公司Eletrobras的专案工程师遭到群众包围,「肩膀被割了一道很深、血淋淋的伤口」。巴西联邦政府的检察署认为水坝计画的环境冲击报告书有瑕疵,也未充分咨询当地原住民的意见,因此提出一系列诉讼来阻止水坝工程,这等于是让一个政府部门正面对上了另一个政府部门。诉讼案件一路缠讼到最高法院,但判决被暂缓,而贝罗蒙奇水坝工程被准予继续。
就算这个复合建设只有两座水坝,但道路的辟建,以及估计会涌入的10万名工人和移民,仍将对辛古河流域产生巨大的影响。水坝将淹没比两个台北市还大的地区。官方预估将会有2万人因此被迫迁徙,独立评估的数字则比这个还高出一倍。此外,被水坝淹没的植被会产生甲烷,释出相当于火力发电厂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辛古河有一条100公里长的河段将有大约80%的河水被分流到水坝中,让仰赖季节性洪水、也是许多濒危物种赖以为生的地区因为缺水而干涸。
「现在的重点是接下来会怎么样,」薛兹曼说。 「政府只说贝罗蒙奇水坝会续建,但原本的提案中还包含了另外五个水坝,问题就在于,光靠一座贝罗蒙奇水坝能否符合成本效益,或者政府之后又会说:我们还是得盖其他的水坝。」
大酋长即将抵达肯强村的早上,二十几名坦着胸脯、穿着黑色底裤、挂着彩色串珠的凯亚波女性围在中央广场周围吟唱、踏步,像是在进行彩排。下午4点左右,飞机声吸引了一群人涌到小机场去。
罗普尼、米卡隆提,以及另一名来自南方的酋长乌帖一同下了飞机。罗普尼是仍戴着唇盘(能扩张下唇、像煎饼般大的桃花心木盘)的五名凯亚波长老之一。他携着一根形状有如中世纪木剑的战棍。他站在飞机旁,一名女性上前握住他的手,哭了起来。若在其他文化里,她可能会被保镳拉开,但罗普尼似乎不以为意,还跟着一起哭了起来。那悲痛的哭泣为的不是最新的灾难,而是凯亚波人的一种仪式,为了失去共同的朋友而哀悼。
当天晚上,罗普尼在男人的集会所里对肯强村民发表演说,在凯亚波语滑降式的语调中,他的声音在好几个八度间起伏。他在空中挥舞双手,又拍打手中的战棍:「我不喜欢凯亚波人模仿白人文化。我不喜欢金矿工。我不喜欢伐木工。我不喜欢水坝!」
他来到肯强村的目的之一,是想了解为什么在领域东边的酋长会接受国营电力公司的金援。好几箱25马力的全新船用马达就堆在「保安林协会」的总部阳台上。罗普尼的村落,以及其他南方村落一直都拒绝接受电力公司给的钱,根据行动人士的说法,这些钱的用意是要减低原住民对贝罗蒙奇水坝的反对声浪。建造水坝的财团一方面出资在该地区凿井、设置医疗站及铺设道路,同时每个月支付约1万5000美元给附近十几个村庄作为食物和补给品的花用金。薛兹曼说这笔钱是「封口费」。
凯亚波人最初收到这些肮脏的巴西钞票后,就为金钱创造了一个发人省思的新字:「皮欧卡普林」,也就是「可悲的叶子」。凯亚波人的生活里出现了愈来愈多可悲的叶子,尤其是在与巴西边境城镇接壤的村落。在图库马附近的凯亚波村落图雷强,林地皆伐和牛只放牧所造成的污染已破坏了当地渔场,而凯亚波人到超市购买肥皂和冷冻鸡肉的景象也并不少见。
有三个晚上,普卡提里都带着罗普尼、米卡隆提和乌帖光临我们的营地。他们坐在校舍阳台上,点燃烟斗,啜饮咖啡,讲述故事,吸血蝙蝠在萤光灯泡昏暗的光线中漫无方向地乱飞。 「从前,男人就要像个男人,」罗普尼说。 「他们被当成战士养大;他们不怕死。他们不怕说了就要做到。他们用弓箭对抗枪。很多印第安人死了,但白人也死了不少。塑造我的就是战士的传统。我从不怕说出我的信念。我从不在白人面前感到耻辱。他们必须尊重我们,但我们也要尊重他们。我相信战士的传统依然存在。凯亚波人若受到威胁就会再披战袍。但我一直告诫我的族人:不要去刻意挑起争端。」
酋长离开的那天,有一些国家印地安人基金会的信件需要他们签署,才能授权进行讨论过的事项。对西方世界与丛林世界同样熟稔的米卡隆提很快签了字,仿佛他曾写过1000封信一样。但罗普尼拿笔的姿势很别扭。我知道他的双手有多么善于驾驭其他深奥的技术,也知道他可以多么灵巧地扎出一条棕榈仁皮带、或塞入一片唇盘、或将魟鱼尾削尖成箭头、或以手势强调他的演说内容,为族人赢得了未来;知道这一切,再看着他吃力地拼写自己的名字,实在太令人震撼。在辛古河谷,几乎找不到比这双手更能干的了。但在书写世界里,这名伟大的酋长就像个孩子一样。
六个月后,26名东区的凯亚波领袖齐聚图库马签署了一封信件,誓言不再接受水坝建案财团的金钱:「我们,米宾乌克莱的凯亚波人,已决定我们不要你们脏钱的一分一毫。我们不接受在辛古河上盖贝罗蒙奇或任何水坝。我们的河川无价,我们吃的鱼无价,我们子孙的幸福也无价。我们的奋战永不停歇……辛古河是我们的家园,你们在这里不受欢迎。」
话不知怎地传了出去。那个没有耳洞的白人要前往肯强山。时间是下午2点30分,我们登山队沿飞机跑道的路还走不到一半,屁股后就跟了大约15个孩子,有十几岁的也有更小的,有男有女,他们脸上涂着颜料,带着用旧汽水瓶装的水。甚至有个兴高采烈、不到四岁的小家伙也跟着,他赤着脚,身边没有怕他走丢、怕他被美洲豹吃了、被毒蛇咬伤、或被各种植物的针刺扎伤而跟随在旁的父母。
我们原本呈一路纵队前进,但后来孩子们就超前了,他们成群围在一些高大的灌丛旁,拉下树枝,砍下野生印加果的豆荚。
45分钟后路径转为上坡。灰色山岩出现在上方:都是垂直的山壁,没有裂痕或明显的缝隙。无论从北方、南方或西方,这座山似乎都无法攀爬,但山的东侧则缓降至森林里。孩子们一路笑谈地爬上陡峭的山坡,一会儿跳过木头,一会儿抓着树藤悬荡。一条狭窄的小径沿坡蜿蜒而上,穿过一道裂隙,你得用汗湿的双手攀爬翻过一块大石才能继续通行。
经过一条长长的斜坡之后就到了山顶的圆丘,孩子们全坐在山顶,背后映衬着粉蓝色的天空。我气喘吁吁地跟在他们后方。褐灰色的蜥蜴四处游走。孩子也同样东奔西跑,在崖边张望,无惧于山壁往下直落约150或180公尺、甚至更深的高度。这里没有扶手,没有警告标示,没有成人监管。四岁男孩在深渊边缘蹦蹦跳跳,笑逐颜开的开心模样,就好像这是一年之中最美妙的一天。
当我们开始往山下走时,他又跑到前头去。我忍不住想着大酋长离开的隔天晚上,我们的向导哲提来到校舍营地时,我们问了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活在森林里,还能当个凯亚波人吗?」哲提想了半晌,摇摇头否定了。接着,他用仿佛在讲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的语气补充说:「你还是凯亚波人,但是没有了你的文化。」
过去有些人类学家盲目崇拜文化的纯粹性,而对现代科技的引进感到忧虑。但文化就跟物种一样会随着机会演化(北美洲大平原印第安人最具代表性的标志:马,就是来自西班牙人),而稳固的传统文化会撷取其他文化的优点,做出有利于未来存续的改变。我们可以质疑一个戴着鹦鹉羽毛头饰、穿着阳具护鞘的男人,是否真的比穿着蝙蝠侠T恤和运动短裤的人更有价值。但是我们如何能漠视凯亚波人对于森林里动植物的丰富知识,清澈水质、纯净空气的无比珍贵,还有多样性本身所提供的基因和文化宝藏?
关于亚马逊森林的最大讽刺是,那些理论上很文明的外来者,在花了五个世纪传福音、剥削及消灭原住民之后,现在又要依靠这些最早的住民,去拯救对这颗星球的健康至关重要的生态系,去捍卫那些不可或缺、未经开发的土地,不让它们受贪得无厌的已开发世界破坏。
我那位四岁的朋友(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早在我步履蹒跚地回到轻松好走的飞机跑道以前,便已一路跑回家了。天几乎要黑了。他妈妈可能已经把他丢到电视机前观看凯亚波仪式的影片或巴西肥皂剧。对他来说,也许这一天并没有特别欢乐,跟其他日子比起来,也没什么特别不一样。不过,对于一个这种年纪的孩子而言,我很难想像得出还有什么样的生活能比以森林为家、当个无拘无束的凯亚波人更完美的了。愿他就这么长长久久地跑下去。
撰文:奇普.布朗 Chip Brown